疫情下的他者哲學:一場全世界都加入,名為「倖存COVID-19」的行為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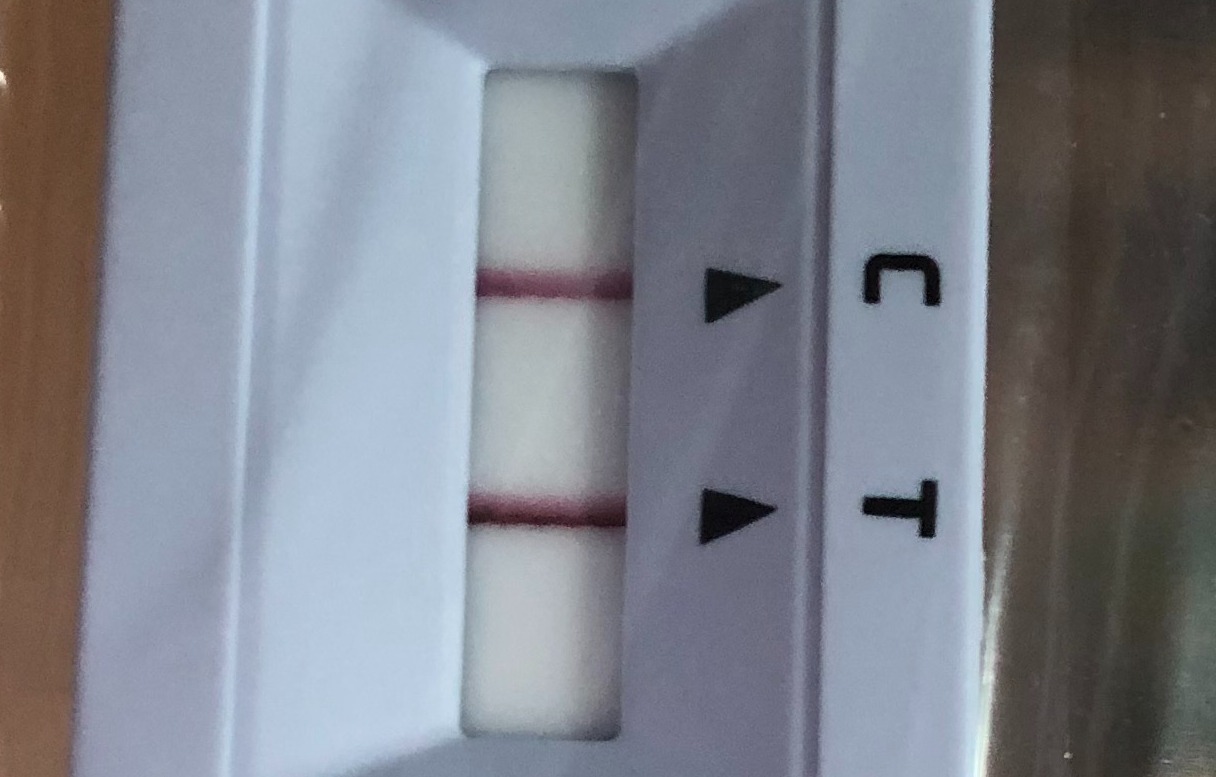
居家隔離的日子,我讀不下任何「克服恐懼」的懶人包。作為心理師,目前對自己實在沒有更好的心理治療。我倒是服了行為藝術家謝德慶和哲學家列維納斯給我的「鎮定劑」⋯⋯
「指揮中心關懷,請問您目前身體健康狀況,一切正常,請回1,有發燒、喉嚨痛、流鼻水、咳嗽、呼吸困難、嗅味覺異常、腹瀉,請回2,其他症狀請回3。」
指揮中心從早上8點連傳了四封簡訊給我,我因為這幾天居家隔離而睡不安穩且失眠,早上錯過指揮中心的訊息,趕緊回覆。一位同事因為關機,指揮中心找不到人,派警察找同事,真的是防疫如同作戰。同事確診後,同辦公室的人都被匡列採撿、居家隔離了。
那晚9點半,主管打電話問我身分證字號和地址等基本資料,我心中覺得奇怪,為何這麼晚要問這些基本資料?我回答完基本資料後,主管說辨公室有人確診。巨大恐懼浪席捲我,我開始了我的「海上」生活——居家漂流的生活。剛好我的充氣墊很像大海,躺上去一直搖搖晃晃的發出聲音,好像有人在求救一樣。
我看著一家便利商店公布的確診足跡,確診者去的便利商店是我和他一起去的。對別人來說這僅是眾多確診者足跡之一,但一旦和確診者接觸,或本身是確診者、居家隔離、集中檢疫或住院者,這個人的內在經驗跟旁觀疫情的他人之間,彼此將產生分裂,是孤獨和恐懼的裂痕。
指揮中心問我症狀的時候,我總是猶豫不決,不知道如何回覆簡訊,是1是2還是3?我跟自己說,頭痛和流鼻水是每次月經來之前的經前症候群,不是症狀,不要嚇自己了,那要回報指揮中心什麼?我沒發燒,有時流鼻水,所以我是不是染疫了?心中反覆問自己,反覆的煩躁和恐懼,一直安靜不下來,放了靜心音樂,點了精油,開始寫作,但只要一收到訊息,傳來同事確診,又開始害怕想哭,情緒在煩躁-恐懼-悲傷-靜心中輪迴⋯⋯
住在美國的大學心理系朋友,在我辦公室有人確診前,傳來暖心訊息「一切小心,平安最重要。」我和她說「好的,謝謝關心!」「身邊到處都是恐懼的蔓延⋯⋯」。我問朋友「美國好嗎?」她說「現在有疫苗已經好多了,希望台灣可以趕快買到更多疫苗。」我和她說「我要打醫事人員的公費疫苗了。」她說「太好了!」我謝謝朋友的關心,互道晚安後,我收到主管的訊息說同事確診了⋯⋯
謝德慶:把疫情下的心境,跨時空超前部署出來
剛開始隔離的夜晚,我都睡不著,被不安與恐懼壟罩,我想起了藝術家謝德慶的兩個先知之作《籠子》和《繩子》。剛看到謝德慶的《籠子》時,覺得他真的是一個自虐者,同時是一個自戀者。他為自己建造一個《籠子》,在1978-1979年,整整365天,把自己關進去一個3.5×2.7×2立方公尺的木籠子。有一位好友會幫忙謝德慶送餐,會幫他清理黑色桶子裡的排洩物。謝德慶當時甚至不符合居家隔離規則,他沒浴室!他在創作聲明在籠子內不閱讀、寫作、不與人交流,他沒聽收音機和看電視,沒有任何娛樂和消遣。後來他忍不住開始在牆壁上刻日子。
「我並不是一個平靜的人。我從不問如何度過時間,我只是度過時間而已。」
謝德慶
我一開始被謝德慶吸引是因為我對他百思不得其解。我去過教養院、精神病院、感化院這些監禁的機構,看過一張又一張呼喚我、感應我的面容。謝德慶是瘋了嗎?做一個籠子把自己關起來?如果你曾看過精神病院裡的白牆上,那些像是被刻上去、一抹又一抹打蚊子留下的血跡,那是精神病人隔離的歷史記錄。
在被居家隔離失眠的夜晚,我不知道如何思考和感受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帶來的生活劇變。我馬上就要關起來了,我的計劃、我的未來、我的強迫症個案會不會因為我居家隔離,懷疑我曾傳染病毒給他?他是否擔心被我傳染而強迫清潔症狀加重?我是不是不小心把病毒傳給他?誰會被我傳染?我不安、恐懼、不知所措,我在恐懼和恐懼中換氣的瞬間,在謝德慶的作品中得以想像、思考和感受居家隔離的生命處境,謝德慶的作品成為居家隔離的「鎮定劑」。
每個人都是另一個人的人質,《繩子》的構成,透過這種將自我託付給他者的時延運動。
《現在之外:謝德慶生命作品》頁51
《繩子》是另一件謝德慶非比尋常的作品。謝德慶和一個看過他展覽,欣賞他創作的女藝術家Linda Montano用一條繩子綁在腰際(去頭去尾約5.5英尺[1.67公尺],相近於疫情下的社交距離1.5公尺),共同生活一年,不管做什麼都要在一起,像連體嬰一樣生活。謝德慶在作品聲明處寫下:
We will stay together for one year and never be alone.
We will be in the same room at the same time, when we are inside.
We will be tied together at waist with an 8 foot rope.
We will never touch each other during the year.
謝德慶彷彿先知,把疫情帶來的心境,跨時空超前部署創作出來,在謝德慶的《現在之外:謝德慶生命作品》裡,記錄謝德慶受訪談《繩子》和《籠子》兩件作品:
我希望做一件事關於人類和他們在生活中與彼此掙扎的作品。我發現被綁在一起是個十分清晰的觀念,因為我覺得,為了生存,我們都被綁在一起。我們沒辦法沒有個別、獨自走進生活。由於每個人都是個體,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關於某些事的想法。但我們是在一起的。因此,我們變成了彼此的籠子。
謝德慶堅持社會關係具有本質性,如同在COVID-19下的台灣人,正在強烈感受人和人之間的連結可以多強烈,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中的隱形繩子,即使我們假裝看不見繩子,假裝自己和陌生人沒關係,但是疫情讓我們假裝不下去了。
謝德慶提到:「這種約束的親密關係會重新制約每一個人的感覺系統,每位行為表演者都無可避免,即使不影響到他們的觀察者,一個人的自我感受必然會侵搭著另一個人的身體狀態。在此,行為表演者投入了一股彼此交互時延的感官入侵或交纏(enfolding), 卻不能讓他們的身體接近碰觸點。」(《現在之外:謝德慶生命作品》頁51)
我在居家隔離我的自我感受,連結於另一個人(同事)的身體狀態。我害怕聽到同事身體狀態的消息,害怕再有人確診 ,我和我的同事間彼此感官入侵和交纏。這不只是我和我辦公室同事的交纏,這發生在每個辦公室、每個家、每個社區、每個角落、全台灣,乃至全世界。
疫情下的他者哲學
「大善(the good)不是已經選擇主體負起人質的責任嗎?主體命定要負起此責,逃避此責就是否定自己。負起責任,他就是獨一無二的。」
Levinas 1991[1974]: 122
伊曼紐爾・列維納斯(法語:Emmanuel Lévinas)是當代猶太裔法國哲學家,提出了一種以「他者」為中心的倫理學,是在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
有藝術評論家認為謝德慶在《籠子》和《繩子》作品裡的倫理學為「他者哲學」。列維納斯認為人應該要走出自己,面向他者,承擔起為他者服務的倫理責任。當我們看見每天的新聞畫面,醫護人員等人一張又一張為了對抗COVID-19而憔悴的面容,每一個對了對抗COVID-19的台灣人臉龐,一張又一張臉刻在我們的心裡。
正如同列維納斯所說的,我們要為他者的面容承擔倫理責任,我們看見了他者的面容。當我們凝視他者的面容,他者則在召喚我們勇於負責。如果你在網路上看到「為了你,我堅守崗位,為了我堅守在家」的標語,你會懂我說的是什麼;如果你在記者會或新聞上,聽到陳時中部長每天語重心長地說要做好「個人的責任」,你就知道個人的責任,以及個人對他者的責任,是對台灣的偉大和重要守護。
我其實和你一樣什麼都害怕,但我知道一切都是值得的。
何云昌(行為藝術家)
居家隔離的日子,我實在讀不下任何「克服恐懼」的懶人包,我倒是服了謝德慶給我的「鎮定劑」。作為心理師,我目前對自己實在沒有更好的心理治療,但我認為在疫情之下,我們要更敏感、更謹慎於「我是無症狀感染者、我是接觸者、我是確診者」,去感受他者的處境和痛苦,提升對他者的感受力,以去除自我持存的生存本質,朝向為他人負責,也使自己關懷的人事物擴大,讓人感受到存在的關懷。
那天確診者同事在我關心他的狀況後跟我說:「我其實壓力很大,我真的很自責,壓力很大,感覺害到大家。」「你一定要好保重,祝福你平安健康,不然我罪過很大。」我告訴同事,他沒有罪過,是我們一起在疫情中安靜修行。疫情帶來的孤獨和恐懼,將被我們的關懷行動所治癒。其實,我們可以想像自己正在參與一場全世界都加入,名為「倖存COVID-19」的行為藝術。
